阿十。一个游荡在教育行业的问题研究者。下面是她的口述,程苓峰增删提炼。
1
北欧和西欧有个教育流派,像华德福和蒙特梭利,可以叫它们素质教育,也可以叫快乐教育。孩子很幸福,在学校里各种玩,织毛衣、做饭,经常去博物馆。
而在中国的学校里就一件事,学习和考试。所以很多人想把欧洲的教育引进来。
但首当其冲的是资源不够。如果上数学课,一个老师可以搞定五十个学生,他们坐下面安静听就可以。但陪五十个孩子玩,满田野撒欢,高度不确定性的体力活,没五个老师搞不定。
中国 30 万所中小学,只有 1% 能支撑起所谓的快乐教育,剩下 99% 只能唱空城计。这种情况下,快乐教育就等于自生自灭,是伤害。
北京有个 HDF 学校,曾要求学生的家长把整个家搬过去,他们认为学校和家是一体,是不可分的社区。
真的很多家长从东城、西城、怀柔搬到昌平去,在那里建快乐教育的乌托邦。这些家长都有经济实力,有钱供养一个乌托邦。
但学校有断档,没有初高中,所以孩子最后还是必须回到体制内,就算要出国,也得去国际学校,还是要学数理化,要考试,要被评价。
很多孩子适应不了,他们无法理解那个新环境,那些新规则,需要重塑三观,然后有挫败感,出现心理问题,会抑郁。一棵树被移植,它面对新土壤,身体会排异。
HDF 这样的教育理念在欧洲搞得好,因为它本来就是那块地长出来的果子。西欧和北欧,人少钱多福利好,而且是相对单调的社会。中国一比,还是人多钱少,是多样复杂社会。
出海,在陌生环境里冲撞,能认识自己。但反个方向,把国外的东西拿进来,也会冲撞,也能认识自己。
大理也有些类似的学校,听起来很诱人,但其实是父母这一代人的代偿心理。
他们的青春期被快速的工业化榨干,没享受过那么自由的生活,他们自己需要被宽容,被友爱,所以想给孩子创造那样的环境。
大理这个城市本身就有气氛。一些人卷不动了,要躺平,为了给躺平找到正义感,所以不知不觉的,对主流社会生出鄙视,觉得你们这些牛马没生活,也没自由。他们反倒觉得,逃离就是牛叉,但其实也是心理乌托邦,很变态。
几十年改革开放,养出来一批富二代,想逃离把他们养大的现实。很多有钱人润出去,在那边闲的蛋疼,天天烧烤,在院子里除草,最后老婆留在那边陪孩子上学,老公又回来,继续挣钱,继续喝酒打单。
大理还个学校,名气大,规则是家长要抱团形成一个社区。但恰恰在这群人里,离婚率之高,一个孩子的父母分开,又跟另一个孩子的父母搞上,在圈子里的名声极其恶臭。以自由之名,敞开变态。
大理有些村子,北上广深的移民搬进来,五六个孩子凑个学校,这个爸教数学,那个妈教美术,但这些孩子缺乏足够多的同伴,缺乏比较,缺乏竞争。
五六个孩子是不够的,要几十几百,丰富性才及格。这样的丰富性只有社会才能提供,只有社会本身是系统的。样本少了,多样性少了,就没有力量。必须把环境参数提高十倍,组织的力量远大于个人。
在欧洲,在家教育的孩子,可以随时中断,随时去学校,也可以工作之后再回去上学,那个社会的供给非常灵活,流动性很强。但在国内,一个手续就要跑很久,一个考试就会卡住,别人的常态是我们的非常态。
移植其它土壤的教育体系到中国来,其实忽视了 “系统性” 的价值。没有一样的社会环境,没有一个场域去配套,树苗长不出来。
最简单粗暴的指标,人均 4 万美金 GDP 的教育模式,很难复制到 1 万美金的社会。如果强行复制一个小环境,但强扭的瓜不甜,它会变种。
在巴西、泰国这些人均 GDP 一万美金上下的国家,也有引进欧洲的教育模式,但只是小部分人的狂欢,没有获得全球化的成功。
就算在人均 GDP 比欧洲高的美国,欧洲的教育模式也是特例。美国的教育是二元,要么穷,要么卷。
直到奥巴马做总统,才提出不要让一个孩子掉队,搞社区大学,以前都是放羊。但美国是州立制,每个州有自己的想法,在大部分时候的大部分地区,底层被放弃掉了。
美国当然有卷,但它是卷科技,像马斯克给自己孩子建的学校,不是欧洲的卷自然。
日韩跟中国很像,很卷,一直干不掉培训班,就算这些培训班绑架了大部分家庭。
中国社会非常多样化,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流派的教育模式,都有一点,分散在不同的人群,没有共识。好像中国的地形,三级阶梯,东南西北,高原丛林和海洋戈壁,全不一样。
东南亚是躺平模式,但跟欧洲也不一样。热带的人,有一顿算一顿,无所谓,因为物产不匮乏,食物充足。
我曾经问一个印尼的局长,印尼人是乐天派,但印尼有海啸,你们会不会恐惧。他说,海啸过后重建就可以了。
以色列是被战争塑造的国家,我曾在以色列一个街道吃饭,隔壁街道有炸弹爆炸了。这种环境塑造了以色列人,第一是及时行乐,第二是更努力。
以色列不存在欧洲教育,只有天才教育,给最聪明的人最前沿最刺激的课程,跟美国一样卷科技。中国其实也是天才教育,在激烈的应试教育里过独木桥,把天才筛出来。
天才之所以是天才,就是他经过了应试教育,但他的活力不会被摁死。而且应试教育夯实了基础,让他的天才更能施展。
在中国,天才多在三个领域,金融、企业和政府。金融只是辅助性行业,本身并不创造新东西。所以做企业的人比他们天才。做金融的人飘在空中,做企业的人顶天立地。
但做企业并不为整个社会兜底,商业产生大量副产品、副作用,而最终为社会兜底的,为所有副产品、副作用买单的是政府。他们更强。
2
中国的教育出海有三个阶段,第一阶段是做华校,孔子学院这样的。但是单点的,容易被连锅端掉。
后来思路变了,到第二阶段,跟着一带一路出去,从基建开始做,比如在东南亚一些国家,把国内的网 + 屏带过去,帮他们建这些基础设施,做教育信息化,一直到内容,到教师的培训。
还给钱。比如需要一个亿,我们官方和企业一起,给你 3000 万,借你 3000 万,再投你 3000 万,你自己出 1000 万。人家礼尚往来,把中文考试纳入到国民体系里去。
它从基础设施到骨架、血肉,都是中国人帮着建起来的,就很稳,想端掉整个体系基本不可能。在东南亚和南亚,除了印度和越南,其它国家都没有自建教育基础设施的能力。
这有点像一带一路的港口,我们帮助建基础设施,就能用上我们自己的标准,做了 “车同轨”,还顺势设计港口运作的规范,以及代运营,那是 “书同文”。
中东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,把中文纳入中小学教育,它们觉得美国太霸权,相比之下,中国有很强的未来,但没有攻击性,像邻家大哥。
在东南亚,上流圈层有 1/3 愿意把孩子送过来,以前是来读大学,现在中小学也多起来。因对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综合认同。
在东南亚,年轻人喜欢泡泡玛特,喝雪王。雪王比当地饮料贵,也比雪王在国内贵,相当于当年我们在国内吃肯德基。他们排队喝雪王,觉得酷,很 fashion。具体讲不清楚,就是感觉。
今天到了第三阶段,就是民营的教育科技企业,自发出海。
2014 年我们组织中国的教育科技企业去美国,有个印度人做分享,就说我们不想分享给中国人,因为你们是 copy cat。
思想都是从高维度流向低维度。显然当时觉得美国欧洲是高维,我们是低维。但很快,也就是几年,情况变了。
芬兰对自己的基础教育不满意,因为很多年没出过诺贝尔奖。它是放养,孩子天天在地里混,数学不好,到了大学搞不定微积分。
中国人还没到密集拿诺贝尔的阶段,但数学是最好的,所以芬兰把中国人的题海战术拿过去。在一定压力下,学习、测试、反馈。强化训练。
有家 app 进了美国的公立学校,不只教他们语文,也教他们英文。中国的科技教育出海去其它国家并不稀奇,但进美国是标志事件。教美国人中文也不稀奇,但教英文也是标志事件。
还是因为我们的训练系统好使,做题、反馈、掌握知识点,起效快。所以会说英文,跟拿到考试结果,它不是一个东西。
中国人擅长工程化,其实就是效率的落地。在文化上它是实用主义。今天这种文化和工程能力,反向输入美国和欧洲。
因为中国是个复杂系统,不是一马平川,也不只有高山峻岭,而是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有,然后什么样的文化都有。
也经历了频繁的战乱,一边内斗一边融合,所以中国人,一上来就要处理一个复杂系统,要从中光速抽象出最简方案。
中国的根是农业。农业几千年都是同质化,每年增收 1%,不会有突变。农民习惯的是重复,精耕细作。
陆地是静态的,海洋是动态的。陆地要求稳定的秩序,有固定的节律去做事,农民对土地重复的管理,其实就是工程化。
而海洋是不确定的,它适合创意,它习惯不一样的东西,而不是年复一年不变的东西。
福建是中国各地区里出海历史最悠久的地方,好玩的是,福建也是教育最不卷的地方,双减政策见效最快的地方。只要妈祖同意,他就出海去,没必要非要读书。
欧美创业者会探索深度,细腻,优美。他们喜欢只做一个品类,比如只做零到三岁,只做编程,更探索教育本身。
我们的创业者更喜欢复制,效率更高,更吃苦,更耐操,但没有生活。大年三十晚上一样找得到人聊工作。
在海外,除了印度人,中国人都打得过。肤色浅的那帮印度人,基本是婆罗门和刹帝利,他们跟中国人一样强,但英文更好,在欧美体系里更能混。
中国人宗教性比较淡,三分天注定,七分靠打拼,不服气。天道酬勤,天道酬善,中国人靠这些规则把人和天统一起来,天人合一了。我们对天不是仰视,他把握了天的好恶。
康熙末年九个儿子争皇位,朝局复杂动荡。邬思道对皇四子胤禛说,不争就是争。这是底层战略。这个皇四子就是雍正。不争就是争,中国人把二元对立统一融合起来。
教育和商业本来是分开的。有不少人,最开始是做公益,追求公平,去支教,建书屋,但太耗时间。所以开始做线上,做推广,做一对多,把效率提上来。
然后又发现很费钱,做不长久,就开始商业化,赚钱越多,就能支撑更广泛的公平。教育和商业统一起来了。
有些创业者,刚开始讨厌大班,讨厌整齐划一,想改变它。但深入之后,也搞融合。他们激发孩子的兴趣,有兴趣就学的更好,考高分就是个结果,这个结果能带来好前途。兴趣和考试统一起来了。
双减前,科技教育企业的 CEO 不关心政策,觉得在这个领域里,政策是空白的,所以只追求市场化。但双减后,他们意识到经济不可能自成一体,在一个社会里,任何东西都是系统的一部分。
既然是一家,就要把大小王分出来,分出来后,小王有小王的自由,也有小王的快乐。这些人从石猴子变成斗战胜佛。双减是堂课,让企业家学会去理解,在政经的立体结构里找方案。
创业者里 80% 是二婚。大部分人离婚,是因为在创业最难时没扛住,就分了,创业总会牺牲掉一些东西。
也有少部分离婚,是成功之后,跟原配的认知不在一个维度上,所以去找更适配的。但二婚的人更快乐,好像升华了。
来源:公众号:程苓峰
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zhangzs.com/533463.html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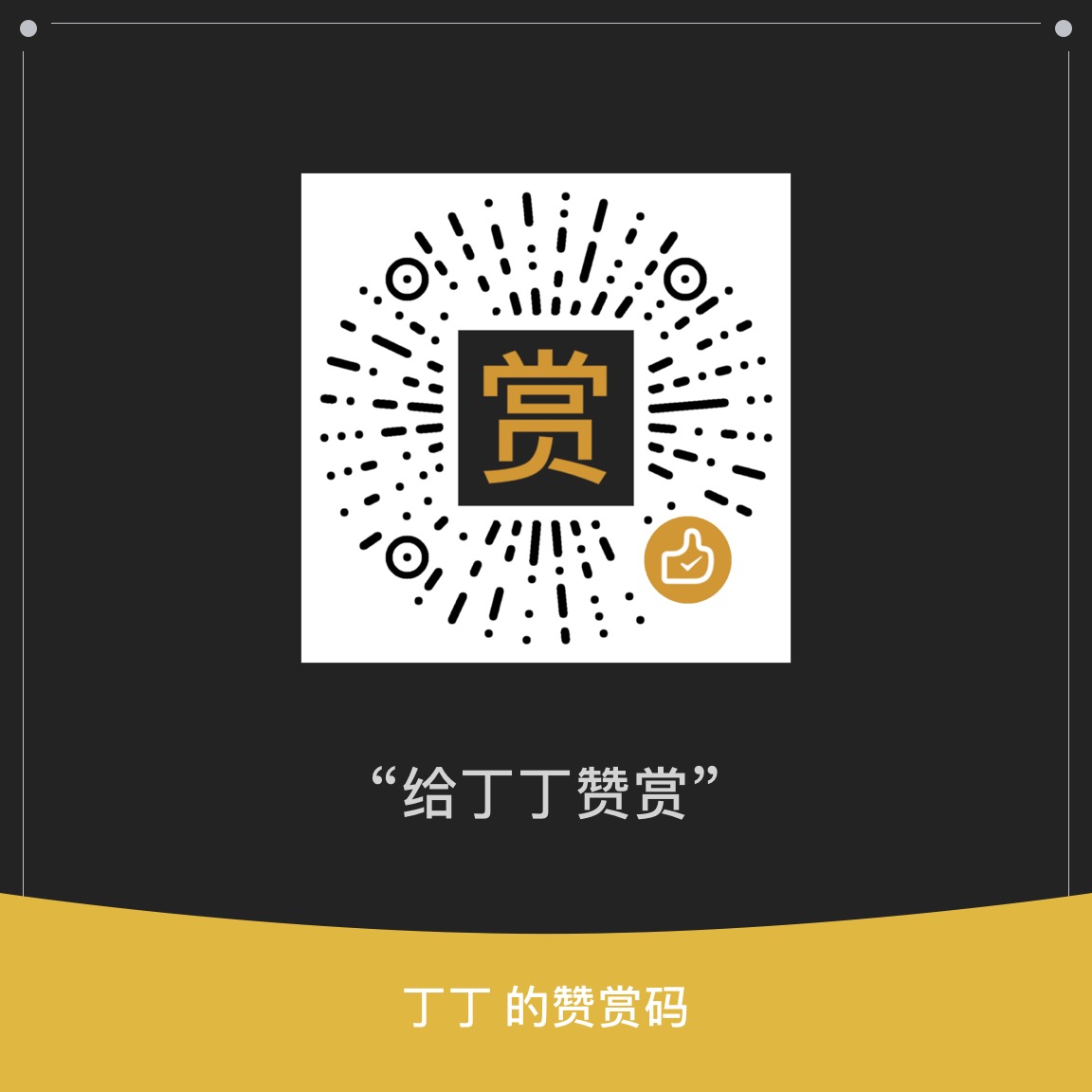 微信扫一扫
微信扫一扫 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