@梁州 Zz:经常看到有网友说,所有末世、囤货、天灾文的鼻祖,本质上都是鲁滨逊漂流记。
的确,所有流行的囤货文、末世文、基建文、种田文、美食经营文,都具有一种同类型的相似性 —— 讲述一个 “被抛入荒原” 的人,如何在困境中重建生活,从无到有地搭建自己的安全屋。而这正是笛福在 1719 年的《鲁滨逊漂流记》中,为后世小说构建的最早的 “安全叙事” 母体。
笛福写《鲁滨逊漂流记》时,正处于一个极端的、不确定的时代。17 世纪末的英国,刚刚经历了内战、政变、瘟疫与火灾。而丹尼尔・笛福本人,则是一个拥有着多重身份的作家,他既是商人、传教士,也是政论家,亲历了伦敦大瘟疫与多次金融崩盘。破过产,甚至坐过牢。在频繁的社会剧变中,笛福一再体会着 “所有秩序瞬间崩塌” 的无力与恐惧瞬间。
于是,“鲁滨逊” 应运而生。一个落单的中产,在荒岛上孤身一人,用勤劳、智慧与理性建构出一座属于自己的 “理性堡垒”。
开局,鲁滨逊落难荒岛,第一时间便开始捡拾物资、分类囤货、清点资源。他在暴风雨后反复登陆残破的船只,把能用的工具和食物都搬运上岸,开始构筑自己的安全屋。因为知道自己可能会困在这座孤岛上很久,所以尽可能用秩序对抗混乱 —— 把食物晒干,挖洞储水,搭建遮风避雨的庇护所。
他记日记、修围墙、驯养牲畜、种植农作物、修复工具。虽然没有 “异能”,也没有 “系统”,但与后世的 “末世天灾囤货文” 所相似的是,他们都拥有的对「确定性」的渴望。
今天的我们,太熟悉这种剧情了。主角穿越到一个荒芜的世界,靠自己一点点采集、建设、囤积、创造,最终搭建起仅属于自己一人的 “安全屋”。
这种 “安全屋情结” 背后,其实投射着一种不容忽视的集体心理。马斯洛需求提出,在人类所有的需求中,最底层的两级是 “生理需求” 和 “安全需求”。在资源紧缺、秩序紊乱的环境下,人对 “可控性”“可预测性” 的追求,会变得极为强烈。
而经营文、基建文、囤货文的最大魅力,就在于它们用一砖一瓦、一锄一草的方式,呈现了一个自下而上的 “安全建构” 过程。我拥有火种,我拥有固定的食物来源,我在这片平地上搭起屋顶、修建篱笆,我在无序的世界里造出了独属于我一人的稳定的秩序。
某种程度上说,这其实是一种 “创世”。正如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,往往需要构建一套 “自我理论”,以此理解世界与建立自我的边界。而阅读《鲁滨逊漂流记》与阅读末世天灾囤货文的过程中,能够让我们感到 “舒适” 与 “愉悦” 的,恰恰就是这种可反复体验的 “与世界重建边界” 的仪式感。
而这种仪式,也恰恰回应了当下时代的情绪底色。
过去几年,我们对 “失控”“断裂” 的体验前所未有。在这种背景下,回看《鲁滨逊漂流记》,你会意识到,它并不只是一个 “主角开挂荒岛求生” 的故事,这种情绪的背后,其实是一种更深层的 “社会剥离后的个体重建”。
现代人之所以痴迷这类叙事,不仅是因为这类叙事 “爽”,更重要的是,因为它能够安抚我们的焦虑 —— 那种无力对抗系统的情绪,在逐渐充盈的粮仓、逐步稳固的安全屋中一点一点被抚平。周遭的一切似乎都在慢慢变好。
就像婴儿离开母亲时,需要一个 “安全毯” 作为过渡对象,而经营文、囤货文,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的 “集体安全毯”。我们所幻想的 “安全屋” 与 “生存技能”,本质上与鲁滨逊在记事本上划下每一个 “今天还活着” 的正字,是极为相似的。
我们太需要一个 “可控的世界” 了。哪怕它只存在于小说中。在阅读这类故事的时刻,会让读者短暂地停留在一个能自给自足且建立固定秩序的世界里。周遭的世界愈下沉,手中的 “安全毯” 则愈重要。
因为那是一种在当下极度稀缺的感受 —— 可控的、源源不断的安全感。
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zhangzs.com/532049.html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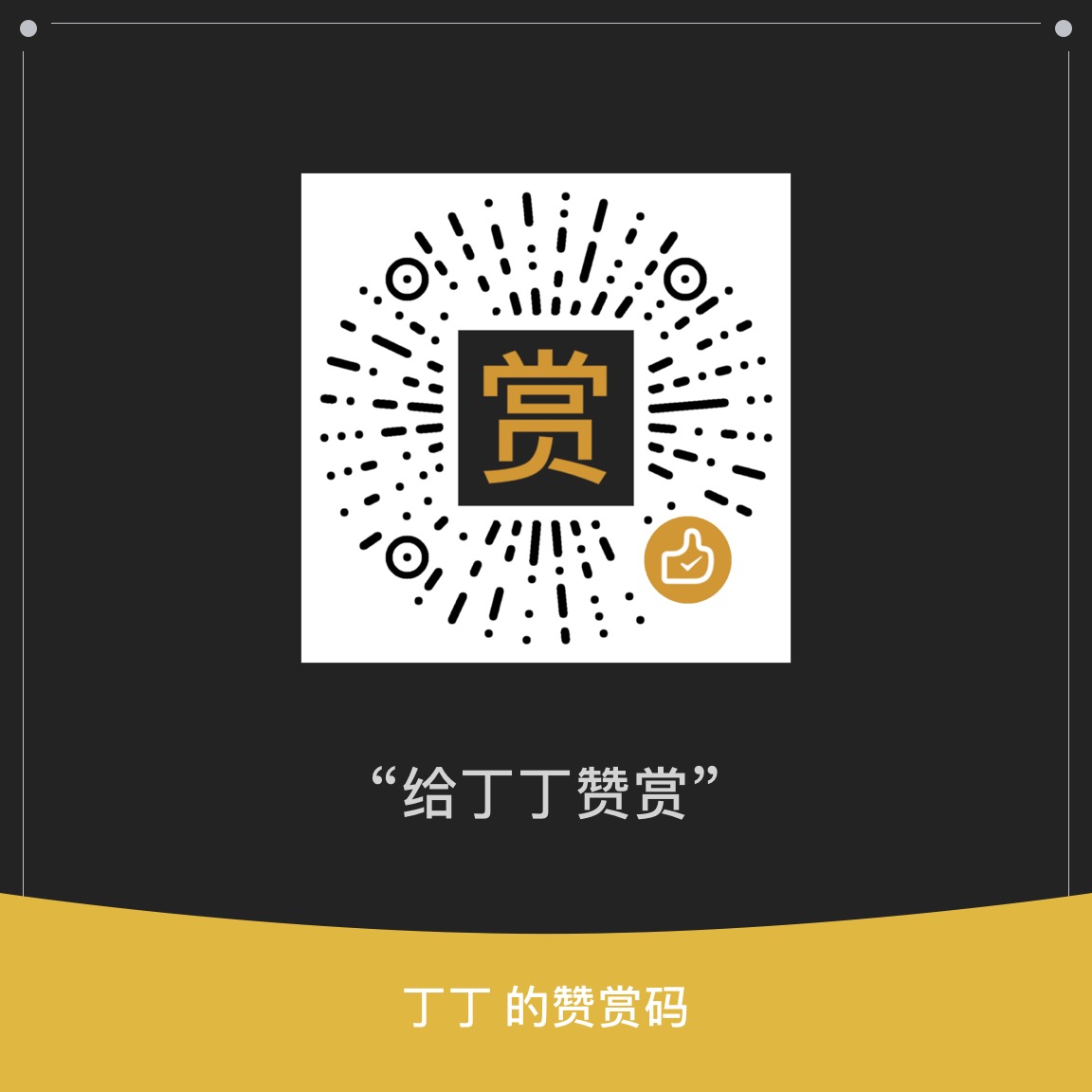 微信扫一扫
微信扫一扫 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