@远东冰原上的猫头鹰:一个就业环境恶化的侧写: 早些年随着大卫・格雷伯的书陆续引进,还有不少对「狗屁工作」的批判。这两年好像很少听到了。「数字游民」「自由职业」经过浪漫化修饰后生产的公号文也没有了市场。取而代之,经常听到的三种表述 ——
1、虽然知道工作狗屁,但害怕跳出后连狗屁工作也找不到,哪怕跳出一年都有危机感;
2、意识到 “我” 在乎的不是工作狗屁,而是工作非但狗屁而且钱少,如果待遇好,“我” 也能发挥出匠人精神;
3、肉身虽活着,但已进入冬眠状态。工作?可以有,也可以暂时没有,靠兼职多项零工、压缩生活成本来度过冬眠期。相应的,越来越多人看电影、买书的频率变少,看短剧等无脑乐东西的时间变多,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。
冬眠时间的主旨是低经济成本与低精神消耗。
另一个现象是,尽管中产阶级缩水,返贫与失业人群比统计数字体现的要更加触目惊心,但技术革命和上一轮政治权力、房地产、互联网、股市及加密货币所制造的巨富集团,财富是进一步增长的。尽管他们在总人群里可能只有 1%—5%,但由于互联网的时髦 APP 推崇成功学叙事,他们及他们衍生的附加群体(如家庭后代、跨国公司高级打工人、技术革命的其他受益者等),仍会营造出仿佛中文互联网有钱人很多的幻觉。
于是,本来在现实世界里,大部分人受结构性剧变影响,连找一个体面的「狗屁工作」都是奢望了。但互联网世界容易制造一种焦虑 —— 怎么他们都那么成功,好像就我掉队了。
但「装体面」和「体面都懒得装了」,可能才是现实世界里更常态的两种情形。
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zhangzs.com/531163.html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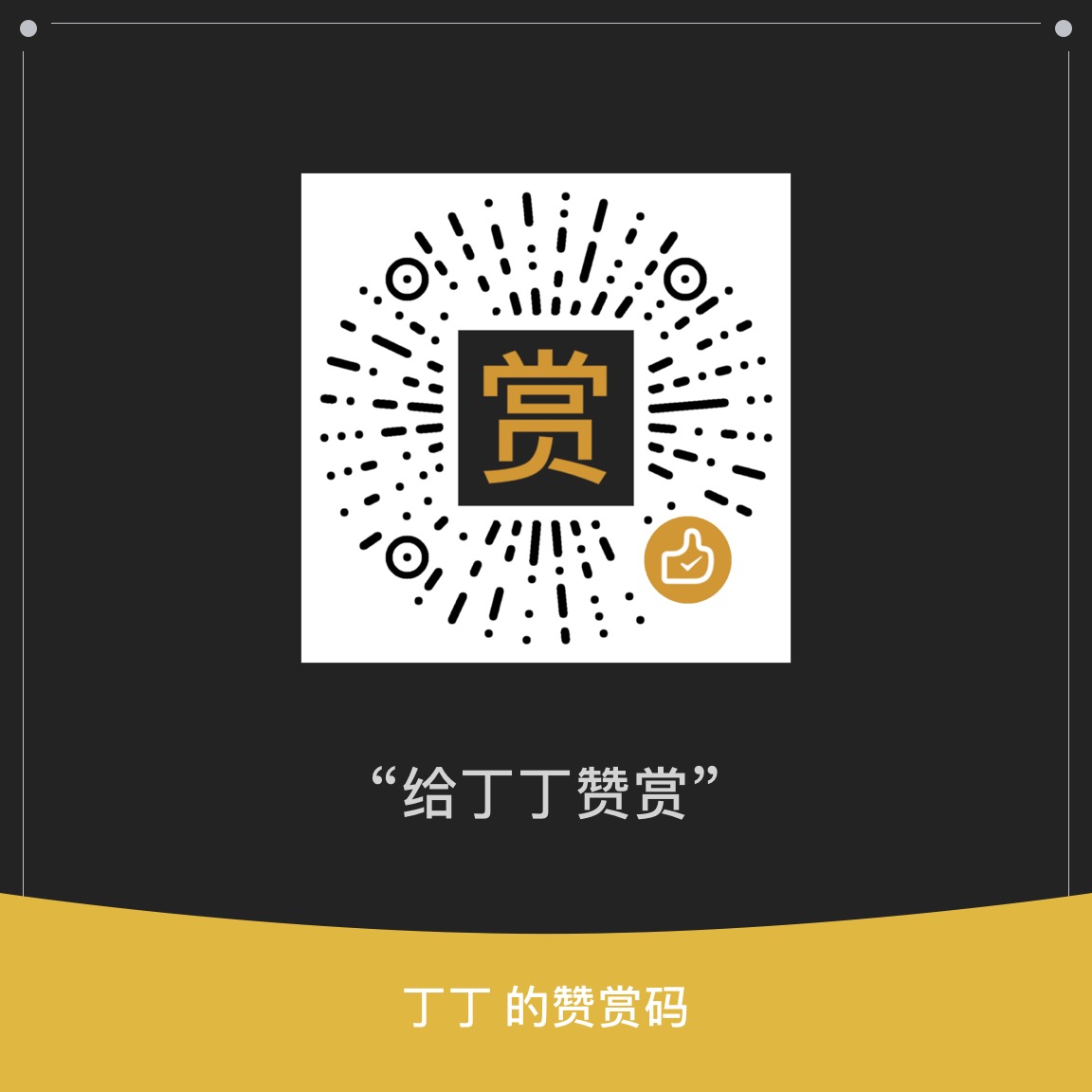 微信扫一扫
微信扫一扫 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