@游识猷:一篇关于中国数字游民社区的论文。
〰️〰️〰️〰️〰️〰️
在西方,数字游民玩的是一种叫做 “地理套利”(Geographic Arbitrage)的游戏,说白了就是:“挣一线城市的钱,过小镇生活。” 一个典型的西方数字游民,可能拿着硅谷的薪水,却住在生活成本极低的泰国清迈。他们是高收入、高消费能力的群体,对社区的需求很明确:提供舒适的服务,我来付钱。因此,西方的游民社区本质上是一种商品,一个为有钱玩家精心打造的付费度假村。
然而,研究者们发现,在中国,情况完全是另一番景象。中国的数字游民群体呈现出一种 “泛化” 和 “不稳定” 的趋势。
首先,他们不一定有钱。 很多人并不是拿着大厂高薪的程序员,而是收入不稳定的自由职业者、内容创作者,甚至是暂时 “躺平” 的探索者。他们的消费能力,远不足以支撑一个纯商业化的高端社区。
其次,他们大多是 “新手”。 很多人还处于数字游牧生活的探索期,被 “诗和远方” 的梦想吸引而来,但对自己到底该如何实现这种生活方式,心里并没底。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服务,更需要指导、社群支持和低成本的试错机会。
这就引出了一个巨大的、根本性的问题:
如果中国的数字游民社区,不能像西方那样依赖一群有钱的 “消费者” 来买单,那它们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?谁来支付那些装修、运营和维护的费用?
〰️〰️〰️〰️〰️〰️
中国的数字游民社区是什么样?
研究者选取了三个代表性的数字游民社区:
▪️ 浙江安吉 DNA 公社: 中国第一个 “网红” 游民社区,由商业资本主导,像一个时尚的创业项目。
▪️ 浙江安吉 DN 余村公社: 紧随其后,但由政府和国企投资,价格更便宜,更像一个 “示范工程”。
▪️ 陕西西安秦托邦: 一个更深入乡村的社区,直接和村集体合作。
〰️〰️〰️〰️〰️〰️
数字游民社区背后,牵涉到的不同利益方:
▪️ 数字游民: 社区的核心,关心的是居住体验、社交氛围和个人成长。
▪️ 政府人员: 关心的是政策落地、人才引进和乡村发展。
▪️ 商业投资方: 关心的是投资回报、品牌效应和商业模式。
▪️ 社区运营方: 他们是夹心饼干,既要让投资方满意,又要服务好游民。
▪️ 村集体和村民:土地的主人,关心的是租金收益和外来者是否会打扰他们的生活。
〰️〰️〰️〰️〰️〰️
▍房产公司商业策划:
第一个吃螃蟹的 DNA 公社,并不是游民们自发组织的,而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爱家地产策划的商业项目。
他们改造了安吉县溪龙乡白茶园一个废弃的竹木加工厂,然后在微信公众号上发了一篇爆款文章 ——《我们在浙江乡下为数字游民改造了一栋房子,然后等你来》。这篇文章的阅读量轻松突破 2.1 万,入住名额瞬间被抢光。
紧接着,像 “一条” 这样的大号跟进报道,推出了《几百个年轻人聚集浙江山里,不坐班,松弛地挣钱》,阅读量直接 10 万 +。
“我是看到一条的报道心动的,视频中社区嵌在白茶村里的景象戳到了我的心窝。我一直旅居国内外各地,成本较高,但 DNA 在村里,生活成本不会太高,加上环境好,于是我就约着认识的游民一起来了。”( D3)
最初的数字游民社区,是一个被商业房地产公司造梦、社交媒体精心编织出来的乌托邦。它满足了城市青年对 “逃离” 和 “田园牧歌” 的所有想象,用浪漫图景吸引了第一批游民。
但是,商业资本的耐心是有限的。DNA 公社面临着一连串的现实挑战:
▪️ 资金有限: 投资方不可能无限 “烧钱”。
▪️ 盈利太慢: 靠收房租什么时候才能回本?
▪️ 模式不清: 除了房租,还能靠什么赚钱?
当最初的网红流量红利过去,如果不能持续吸引足够多的游民入住,或者找不到新的赚钱方法,资本就会考虑退出。
DNA 公社的运营陷入了 “双重困境”:
▪️ 与政府的协商困境: 政府口头上欢迎,但缺乏真金白银的财政补贴和人才政策,缺乏真正有吸引力的制度创新。
▪️ 与投资者的目标错位: 投资者(地产)关心的是利润回报,希望尽快看到钱。而运营者(通常是资深游民)关心的却是社区氛围和细节体验。结果就是,投资者不愿意为那些 “不赚钱” 的社区活动和细节服务买单,而运营者在没有稳定资金支持的情况下,只能 “为爱发电”,难以为继。
“我们是一个商业项目,需要考虑投资回报。DNA 这块地是政府让我们替它去规划,但是没有其他的资金补助,社区的改造、装修都是我们投资的,自负盈亏。社区是特色小镇的一环,虽然暂时不考虑它挣钱,但是也不能一直贴钱,所以现在需要考虑后续的经营方向。”( B2)
〰️〰️〰️〰️〰️〰️
▍政府入场:
DNA 公社的爆火,让地方政府看到了一个新机遇:这不就是我们心心念念的 “乡村振兴”/“新型城镇化”/“吸引年轻人回乡” 吗?
于是,一种全新的模式在 DN 余村、秦托邦等地出现了:
▪️ 老板换了: 不再是追求短期利润的地产公司,而是由政府协调、国企(国投)出钱。这意味着更稳定的资金和更长远的规划。
▪️ 管家也换了: 社区的运营团队,不再是 “为爱发电” 的游民,而是政府或国企雇佣的第三方专业团队。比如秦托邦的运营方,就是当地政府合作的文旅公司。
▪️ 关系变了: 政府和社区的关系,从之前那种 “口头支持、偶尔互动” 的偶然关系,变成了一种用政策、资金、制度牢牢绑在一起的 “深度绑定” 关系。
所有的玩家 —— 国企投资方、运营团队、村集体、甚至数字游民自己,都开始围绕着政府的意图重新组织起来。
社区建设的核心目标,也从 “如何赚钱” 变成了 “如何吸引更多泛数字游民,服务于乡村振兴大战略”。
这种模式最直接的好处就是:便宜,非常便宜。
在政府主导的社区,一个单人间的价格,几乎只有商业社区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。比如 6 人间的月租金从 440 元变成 350 元,1 人间的月租金从 2980 元变成 1200 元。
一位游民(D4):“在乡村来说的话,DNA 住宿并不算是便宜的,单间的价格 ( 1960 元 / 月) 在镇上可以租一套房子。但 DN 单间就便宜很多,设施也比较新,我更愿意来这里。”
政府的钱不是白拿的,它有自己的 KPI。政府希望社区成为一个模范生,一个展示给外界看的示范区。
结果就是,社区运营方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去接待参观,这严重打扰了游民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。
运营方(C3)也很无奈:“因为有补贴,我们也不好说什么,只能规定参观区域,原则上是不让进入游民的私人区域的,但是有些参观者还是会打扰到游民,发生一些冲突。”
〰️〰️〰️〰️〰️〰️
▍隐藏的 “地主”—— 村集体
除了政府、资本和游民,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但手握王牌的玩家 —— 村集体。简单说,他们是这片土地真正的 “地主”。无论是 DNA 公社租的废弃工厂,还是秦托邦租的 200 户民房,最终都得经过村集体点头。
研究者发现,村集体的态度非常微妙。
一方面,他们欢迎游民社区,因为这能盘活闲置的房子,给村里带来租金收入和人气,这是实实在在的好处。但另一方面,他们又很警惕。他们会担心:“这帮外地人会不会把我们村搞得乌烟瘴气?”“他们赚钱了,我们能分到多少?”“他们会不会不尊重我们的风俗习惯?”
以秦托邦为例:
▪️ 模糊的利益分配: 运营方的上级企业,先用一个价格(比如 X 元)从 200 户村民手里统一租下房子,然后再用一个更高的价格(比如 1.1 倍的 X 元)转交给村集体。这个模式虽然盘活了闲置资产,但它稳定吗?村民会不会觉得租金低了?村集体会不会觉得 “过路费” 少了?由于缺乏长期、稳定的支付保障和透明的分配机制,这种合作非常脆弱,随时可能因为利益纠纷而引发 “土地占用矛盾”。
▪️ 文化与金钱的冲突: 村集体的想法很复杂。他们既希望通过出租土地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分红,又很看重土地承载的文化价值。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家园被外来的经营者搞得面目全非,不希望祖辈留下的土地完全受制于人。这种 “既要又要” 的心态,让运营方在进行任何改造时都束手束脚。
▪️ “人情” 大于 “规则”: 当社区运营者需要协调内外事务时(比如游民和村民发生摩擦),他们会发现,村集体这个 “协调员” 的角色,效力非常有限。村里没有一套统一的、成文的规则来处理这些新问题。大多数时候,解决问题靠的不是规章制度,而是 “临时谈判” 或者 “刷脸”—— 看运营者和村干部的 “人情关系” 好不好。这让社区的日常管理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。
〰️〰️〰️〰️〰️〰️
▍文化的稀释 —— 当 “真游民” 遇上 “泛游民”
随着社区名气越来越大,来的人也越来越杂。最初,大家都是 “真游民”,抱着对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向往而来,愿意分享、共创,社区氛围非常浓厚。
但后来,涌入了大批的 “泛游民”—— 他们可能是对游民生活的好奇者,可能是来短期体验的度假客,也可能是纯粹来打卡的游客。他们对社区的公共生活没什么兴趣,也不参与共建,只是把这里当成一个便宜的 “乡村版青年旅社”。
“这里的人特别杂,有采访的,有做研究的,有疗愈情伤的,有大学生来写论文的…… 好像就是没有数字游民。虽然社区尽量给大家提供各类的交流活动,但大家都是交浅言浅地浪费时间。”( D5)
这种现象被称为 “社区氛围的稀释”。原本一个由 “信徒” 组成的紧密社群,逐渐变成了一个由 “游客” 构成的松散旅店。共享、协作、共创的社区文化,正在慢慢流失。
〰️〰️〰️〰️〰️〰️
▍夹缝中的运营者
社区运营者(通常本身也是资深游民)是社区里最累、最 “心塞” 的一群人。他们就像一个家庭里的 “管家”,上有老(投资方 / 政府),下有小(社区游民),还要处理和邻居(本地村民)的关系。
他们的理想是打造一个有爱、有活力的社区。但现实是:
“我和爱家地产是合作关系,DNA 从策划、运营的具体事务都是我们做的。目前 DNA 的现金流都依靠房费,如果爱家不给钱,很多运营创意光靠房费是无法实现的。最近 DNA1000 天活动的费用也还不明确,总体上我是能贴就贴,但是能贴多少呢,感觉是为爱发电。”( C1)
“在实际运营中,我发现政府对我们的指导和干预挺多的,有时候对于工作效率来说负面大于正面,这个东西很撕扯,目前还没有找到合理的处理方式。我觉得理想社区氛围是要和人强绑定的,是怎么为人创造生活体验,并不是一味地开疆辟土,这不是我认为的社区运营。”( D4)
“和村集体、村民打交道仍然停留在最基础的人情往来。现在能做的就是建立信任机制,但过程是长期的、缓慢的。目前我们向村民开放社区健身房,拉村民来健身是融合的第一步,也是信任建设的第一步。想通过社区把外来的年轻人和村民融合在一起,健身是一个接口,天天来,就熟悉了,以后做事也就方便了。”( C5)
他们满怀激情地想为社区 “发电”,但往往发现自己手里既没有钱(资金被投资方控制),又没有权(决策要听政府的),最后只能在各种矛盾中周旋,身心俱疲。
〰️〰️〰️〰️〰️〰️
对游民来说:
你在网上看到的岁月静好,可能是商业推广的一部分。一个社区的真实体验,远不止于几张精美的照片。在被 “种草” 之前,多去打听一下社区的运营模式。问问自己:这个梦是为你造的,还是为投资人的钱包造的?因为当浪漫的泡沫褪去,现实问题 —— 比如资金链、运营能力 —— 就会浮现。
政府主导的社区通常性价比超高,基础设施有保障。但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,你可能不仅仅是居民,还是一个 “活的展品”。你的生活可能会被 “为完成任务” 而组织的各种活动所打断。选择这类社区前,最好打听清楚它的 “接待文化” 和对个人空间的尊重程度。
在选择社区时,不要只看硬件,更要关注 “软件”—— 也就是人。一个社区的灵魂在于它的居民。你可以尝试在入住前,通过线上社群观察一下社区的日常讨论氛围,或者短期住几天感受一下。问问自己:这里的人是我想要交流的吗?社区的活动是我感兴趣的吗?你是想找一个 “一起搞事情” 的部落,还是一个 “互不打扰” 的旅馆?这决定了你的社交体验质量。
📄牛天,陈绚。中国的数字游民社区何以生成?—— 以 “嵌入性” 为视角的探索性研究 [J]. 新闻与传播研究,2025,32 (05):33-45+126-127.
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zhangzs.com/532941.html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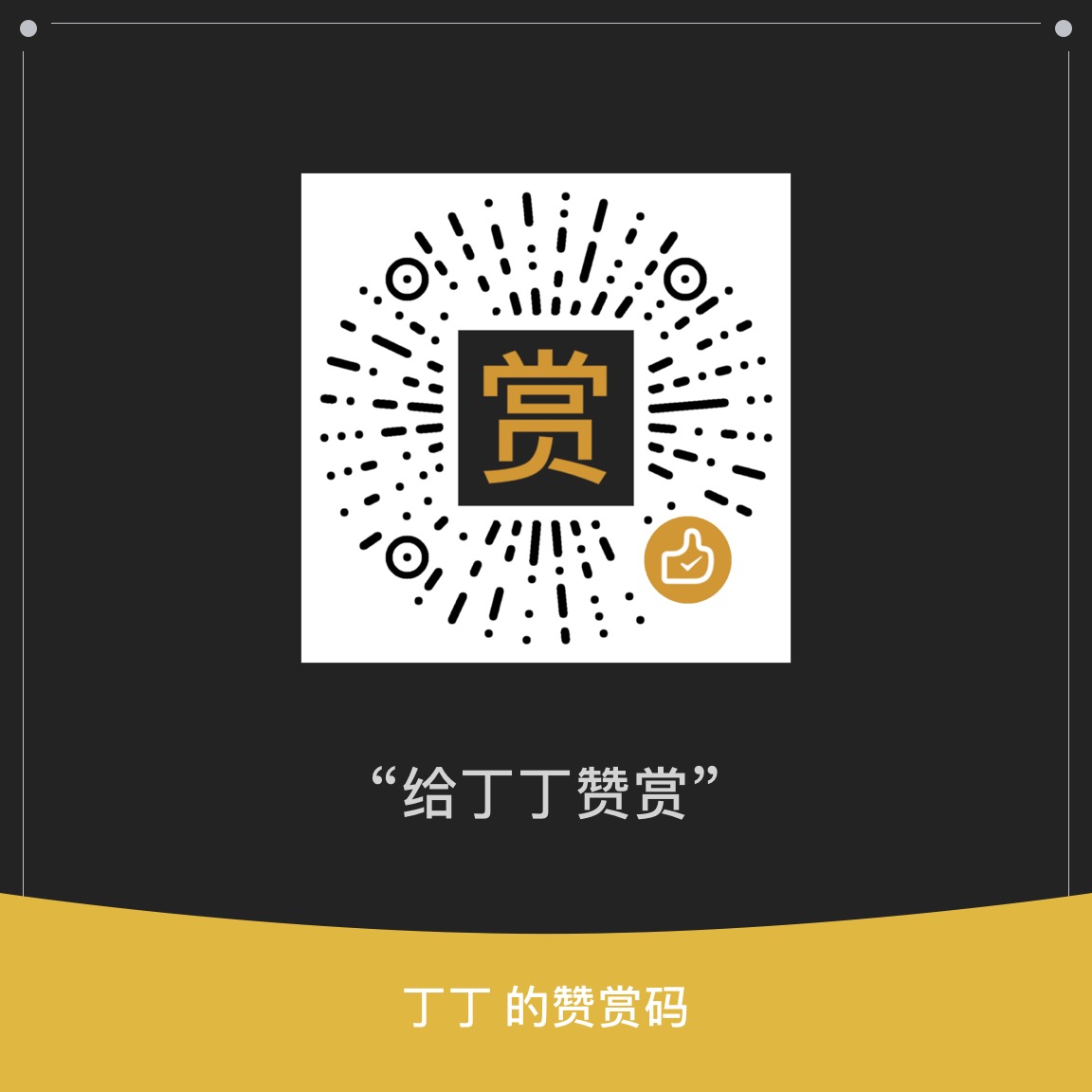 微信扫一扫
微信扫一扫 

